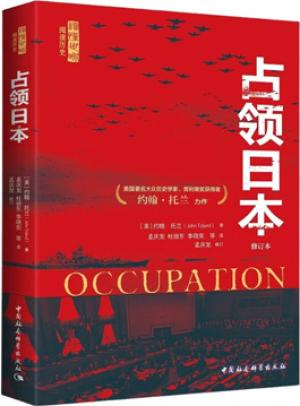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权力意志(全二册。尼采晚年思想结晶;剔除惯性、升华自我的思想利刃)
》
售價:NT$
500.0

《
从领口开始编织的钩针毛衫
》
售價:NT$
301.0

《
日中之光——埃瓦格里乌斯笔下5—6世纪的拜占庭帝国
》
售價:NT$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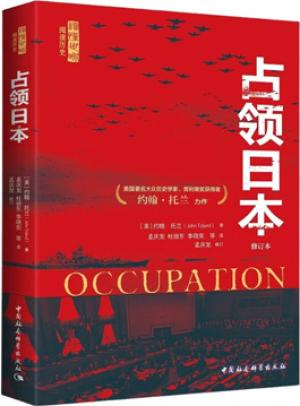
《
占领日本(最新修订)
》
售價:NT$
301.0

《
唐勾检制研究
》
售價:NT$
296.0

《
俄罗斯通史(公元9世纪—1917年)
》
售價:NT$
500.0

《
被争夺的身体:魏玛德国的生育制度
》
售價:NT$
449.0

《
热烈的孤独:大宋词人的明月与江湖
》
售價:NT$
356.0
|
| 編輯推薦: |
百年繁华如何终结?
呈现盛世崩解前的每一道裂痕
一本书讲透北宋王朝覆亡史
北宋历史大变局的前因后果
★ 盛世与危机,有时只差一步
深入解析靖康之变终结北宋百年繁华的全过程,展现悲剧的序曲和终章从做出联金灭辽的决策到收复燕京,再到金宋反目,层层剖析北宋灭亡的深层原因。探讨“联金灭辽真是唯一出路?”“燕京收复是胜局还是催命符?”“金国杀心何时暗起?”“靖康之变能否被逆转?”等关键问题。
★ 立体叙事,聚焦三国博弈
以宋、辽、金三国的外交与军事斗争为主线,展现北宋末年复杂的历史格局揭露三国博弈中被掩盖的致命误算通过赵良嗣、马扩等使节的视角,还原北宋在孱弱军事背景下的艰难外交努力
★还原细节,复活历史现场
立足《宋史》《辽史》《金史》《大金国志》《契丹国志》《三朝北盟会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宋会要辑稿》《宋史纪事本末》《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史籍原典,结合历史笔记、碑文等资料,细致还原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生动刻画宋徽宗、文臣武将及普通百姓在亡国危机中的抉择与挣扎。
★ 对人性与制度的深刻反思
揭示战略迷途、制度腐朽与人性堕落如
|
| 內容簡介: |
本书以北宋末年的历史为背景,从联金灭辽这一导致北宋王朝由和平走向战争的关键抉择开篇,呈现北宋君臣面对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在战与和的泥淖中艰难挣扎,直至靖康之变北宋灭亡的全过程。
从细节入手,通过外交与军事两条主线的交替叙述,结合北宋的外交制度、政治制度等,再现:
以赵良嗣、马扩等人为代表的北宋使节在没有军事后盾支持的情况下,如何与辽金二国展开艰难的外交斗争,并最终收复燕京?
燕京收复后,面对脆弱的和平局面,北宋朝廷如何一错再错,最终引发宋金战争?
战争爆发后,面对金人的进犯,北宋皇帝、文臣武将以及普通百姓分别做出了什么抉择?实施了哪些努力?
是什么导致了北宋的最终灭亡?
立足《宋史》《辽史》《金史》《三朝北盟会编》《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原典,结合相关历史笔记、碑文等资料,细致还原历史细节和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探寻北宋王朝灭亡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对现时代的镜鉴意义。
|
| 關於作者: |
李臣
山东人,青年历史作家。
熟读二十四史等史书,深耕宋史。
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生动的叙事风格见长,善于从细节处复活历史现场,为读者提供专业可靠又不失趣味的阅读体验。
作品见于《青年文摘》《联合日报·文史周刊》等权威刊物。
“写史不为复述兴衰,而为刺破人性迷障。”
|
| 內容試閱:
|
◎书摘:以下书摘作者均为:李臣 著
楔子 大宋外交官
一、朋友、仇敌,还是兄弟?
宋徽宗政和元年 (公元1111年)九月,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
天刚亮不久,大街上已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沿街的商铺已早早开门营业,各式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丝绸、绢帛、瓷器、服装、名人字画、日用百货、各种吃食……甚至从国外远道而来的各种洋货,也大批大批地摆在店铺里售卖,显得稀松平常。
商铺门前,行人如织,往来穿梭。坐轿的、骑马的、牵驴的、赶牛的、推车的、步行的……熙熙攘攘。间或有挑着担子的小货郎穿行其中,测字算命的江湖先生和杂耍卖艺的能人异士也各显神通,吸引人们驻足观看。叫卖声、吆喝声、喝彩声、讨价还价声、欢声笑语声、马鸣牛嘶声……此起彼伏。一派繁华之象!
日头渐高,伴随着一阵杂乱的马蹄声,一支数十人的队伍从高大的城门中鱼贯而出,在随护军兵的保卫下一路向北,向着北方边境线浩荡而去。
随行的马车上,装着各种珍贵的礼物和北宋的土特产,部分人员的肩上还背着装有重要公文的包裹。为首的几人身着官服,器宇轩昂,官服颜色和样式的差异代表了官职品级的高低。就连队伍后方未穿官服之人,也是衣着华丽,一派富足之相。
队伍中几乎每个人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即便称不上英俊倜傥、仪表堂堂,也让人备感舒服,绝无面貌凶恶、贼眉鼠眼之徒。因为他们并不是外出公干的普通官员和随从,而是一群代表着北宋国家形象、肩负国家使命的特殊人员—国信使。
土生土长的汴京百姓对这种大场面显然已经熟视无睹了,他们每年都至少会两次见到这种情形,多的时候见十几次也不算意外。在他们看来,这次出使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大宋使节的又一次正常出访而已。
自澶渊之盟以来,大宋奉行和平相处的外交政策,与周边国家互派使者进行交流已成常态。除在偏远的西北地区与西夏偶有摩擦之外,大宋子民已经享受了一百多年和平。经过数代皇帝的休养生息和鼓励生产,此时的大宋,无论农业还是工商业,无论经济、文化还是科技,都已经达到了历代封建王朝所不能企及的高度。
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写道:“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十一、十二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陈寅恪先生也对宋代文明推崇备至。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世界领先、登峰造极,这就是北宋的高度。
北宋灭亡后,被迫南渡的遗民孟元老抚今追昔,不胜感慨之余,根据自己在汴梁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追忆成《东京梦华录》一书,为我们真实再现了汴梁城的繁华与辉煌: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辏,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国宁人安,物阜民丰。此时的大宋,繁盛而稳定;此时的大宋子民,自信而富足。
大家相信,这样的盛世将会一直延续,这样的生活也会一直延续,一如昨日与往昔。
谁都不会想到,使团远去扬起的尘沙,不仅遮蔽天空,还会掩埋历史。
正是以这次出使为起点,之后的数年间,大宋子民的命运将发生可怕的转折,同时改变的,还有大宋的国运。安定的生活将戛然而止,繁华的盛世将轰然倒塌。而当这场巨变来临之际,无论是渺小的个人,还是庞大的国家,都显得无力和脆弱。
国信使们要出使的国家,是位于国家正北方的另一个大国,由契丹人建立的草原国家—大辽。
受《杨家将》《呼家将》等评书的影响,人们总是认为,大辽与北宋天生就是仇敌,不是你南侵,就是我北伐,打打杀杀似乎从未停止过,鲜有把酒言欢、握手言和的时候。
实际上,两国关系用一个词来形容再合适不过:相爱相杀。一百年前是仇敌,现在是兄弟,几年之后又将变成死敌。双方均见证了彼此从强盛走向衰弱,甚至灭亡的全过程。
如果我们认真计算一下,就会发现,在宋辽两国都存在的一百六十五年间(从公元960年宋朝建立至公元1125年辽国灭亡),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时间都是和平的,两国间的友好交往远大于杀伐征战。
事实上,北宋建立还要感谢大辽。
史载,公元960年正月初一,新年第一天刚刚开始,后周便收到了辽国大举南侵、进犯后周边境的消息。鉴于刚即位的周恭帝还是个年仅八岁的小朋友,完全没有政治概念,只好由宰相范质等人拍板,派赵匡胤率领军队前去反击。没承想走到陈桥驿的时候,士兵突然发生了哗变,胁迫赵匡胤做了皇帝。赵匡胤就这样无辜地成了宋太祖,建立了北宋。
当然,这都是北宋官方说法,辽国方面并无在公元960年出兵南下的记载。所以很多人怀疑,所谓辽国入侵,很可能是赵匡胤团伙编造的政治谣言,以便实施其谋权篡位的阴谋。这一公案,时至今日仍无定论,真相究竟如何,不得而知。
不管怎样,就是从这时开始,北宋开始和辽国产生了联系。
在后面的叙述中,我们将会大量涉及宋辽金三方在外交活动中的精彩博弈与智谋对决,不妨先以宋辽前期的外交为蓝本,大致了解一下北宋的外交程序。
北宋建立以后,并没有立即同辽国建立外交关系。一来是因为北宋继承自郭威建立的后周,而后周与辽国是世仇,虽然现在改名叫大宋了,但土地还是那些土地,人民还是那些人民,仇恨还是那些仇恨,并不会因国号改变而消失。赵匡胤的帝位本就得之不正,如果再着急忙慌地去和仇敌结交,只会更加丧失民心。二来是因为辽国对新建立的北宋政权也并无好感,三天两头来搞破坏,要么亲自来,要么安排“小弟”北汉来,而北宋也总是想把辽国的“小弟”北汉吃掉,导致双方没有开展正常外交的可能。
直到十四年后的开宝七年(辽保宁六年,公元974年),双方才开始外交接触。
根据宋方记载,接触是辽方首先发起的。辽国涿州(今河北涿州)刺史耶律琮给北宋雄州(今河北雄县)知州写了一封情深意长的信,诚恳地表达了想要和宋朝交朋友的良好愿望。信中说咱两家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初无纤隙”),如果能互派使者交流一下感情(“若或交驰一介之使”)、重修旧好,不是好事一件吗(“不亦休哉”)?
而辽方记载则恰恰相反,说接触是由宋朝先发起的,而且是上赶着要和辽国交朋友(“遣使请和”),辽国这才派耶律琮前去“议和”。
究竟谁先向谁示好,因双方政治立场不同,导致记载相左,已无从考证。此次接触的具体细节和内容,也因不载于史籍而无法弄清。但双方的外交接触开始于开宝七年(公元974年),是没有问题的,后世有史家称之为“雄州和议”。
“雄州和议”之后,双方开始互派使节,成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好朋友,逐步建立了友谊。
友谊的保质期,五年。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斧声烛影中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为了强调皇位的合法性,树立自己在群臣和百姓心中的威信,毅然决定柿子专拣软的捏,亲征北汉,铁了心要把辽国的这个小兄弟吃掉。
辽国当然不愿意,立即派人来传话:那是我小弟,大家都是朋友,能不能给我个面子,这事就算了。
没想到赵光义硬气得很,说这事你最好别掺和,那咱还是朋友,不然的话连你一块打。
大辽当然不是吓大的,打就打,谁怕谁!
两国正式断交。
其实在这之前,宋太祖赵匡胤已经对北汉下手好几次了,只可惜自身实力不够,对方又请有外援(大辽),没有一次能占到便宜。最后一次好不容易有了点收获,眼看胜利在即,没承想人算不如天算,赵匡胤突然死了,宋军只好草草班师,无功而返。
事实证明,北汉并不是软柿子,而是硬骨头。不出意外的话,北宋这一次也注定会以失败收场,绝无获胜的可能。
但统计学告诉我们,只要重复的次数足够多,小概率事件也必然会发生(买彩票的朋友就对此深信不疑)。这一次,北宋居然打赢了,虽然有大辽在背后撑腰,北汉还是被消灭了。哥哥用尽一生也未能做到的事,自己竟然一战就搞定了,宋太宗顿时膨胀了,觉得自己无敌于天下,那干脆把大辽也灭了吧!
当年五月,宋太宗亲征大辽。
事实证明,侥幸代替不了实力,大辽东北霸主的地位是不容撼动的,起码在当时是无可挑战的。宋军大败于高梁河,宋太宗本人也挨了辽军一箭,吓得乘着驴车落荒而逃。
为了找回面子,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不顾群臣反对,决定趁辽国皇帝新丧、新主年幼之机,欺负一下孤儿寡母,毅然决定北伐辽国,史称“雍熙北伐”。结果宋军再次大败于岐沟关,《杨家将》中的杨令公原型杨业也在这次北伐中身死殉国。
两次大败,终于让宋太宗认清了现实,既然打不过人家,只好求别人不要来打自己。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宋太宗两次遣使求和,结果都是热脸贴冷屁股,辽国压根不搭理他。
不仅不许和议,辽国还决定要报复一下北宋。宋真宗咸平六年(辽统和二十一年,公元1003年),辽圣宗耶律隆绪和承天太后萧绰(萧燕燕)统兵伐宋。宋军仓皇迎战于望都(今河北望都),大败,副都部署、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力战被俘。谁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个败军之将,间接影响了宋辽今后一百多年的政治格局。
王继忠被俘后,由于消息传递不畅,宋真宗一度以为他战死沙场了,追赠他为大同军节度,向家属发放抚恤金,并为其四个儿子安排了工作。事实上,被俘的王继忠不仅没有受到非人折磨和严刑拷打,还被辽国给予高规格待遇,赐名耶律显忠(后改名耶律宗信),封楚王。
一个异族俘虏竟然被封为王,辽国对王继忠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在后来那个关键时刻发挥出强大的影响力,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从道德家们的角度来看,王继忠被俘之后,不仅没有撞碑而死、以身殉国之类的壮烈之举,还公然接受大辽的官职,甘为契丹人的鹰犬,实在有辱大节,应该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
如果抛开道德说教,单从历史本身来讲,王继忠虽然气节有亏,但对自己的祖国北宋还是很够意思的。史料记载,王继忠虽身在大辽,但终生不忘宋朝,每见宋人必大哭。《四郎探母》中的杨四郎,据说就是以他为原型创造出来的。
望都之战的第二年(公元1004年),辽圣宗和萧太后再次南下。北宋朝廷再次陷入恐慌,以副宰相(参知政事)王钦若为代表的一众大臣被辽军吓破了胆,极力怂恿宋真宗南下逃跑。好在宰相寇準力排众议,说服真宗皇帝御驾亲征,极大地鼓舞了宋军官兵的士气。
与此同时,降辽的王继忠也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他竭力劝说辽圣宗和萧太后罢战讲和,并最终成功说服了他们。
就这样,仗不打了,双方开始互派使节,商量和谈的具体内容和细节,最终于当年十二月签订条约,即《澶渊誓书》,史称“澶渊之盟”。
条约规定宋朝每年要向辽国支付三十万的助军之费(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看上去宋朝吃了大亏,因而后人常将之视为屈辱的城下之盟。
但事实上,三十万的助军费支出,还不到宋朝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比战争造成的损失要少得多。战争不仅要耗费巨额物资(有时候一年的财政收入都不足以支撑一场大战),还会死人。战争破坏和导致的劳动力缺少,又会影响生产(在农业社会这是十分致命的),进而导致财政恶化和社会矛盾增加。历史上很多政权就是这样崩溃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