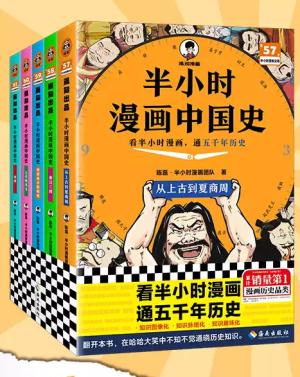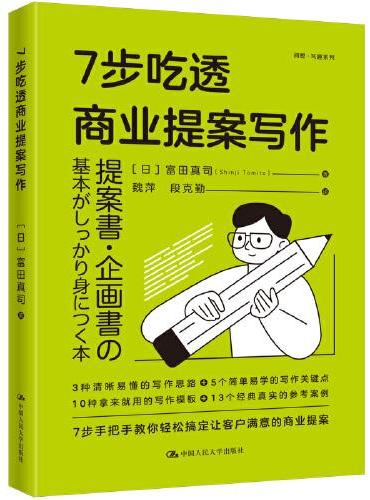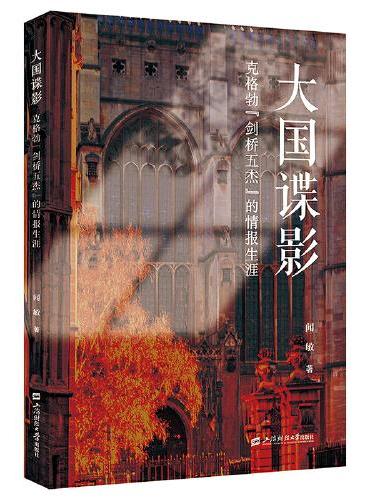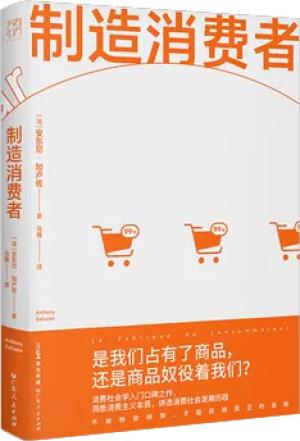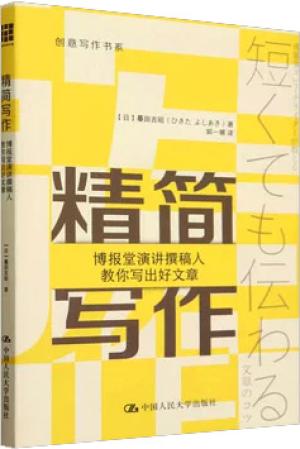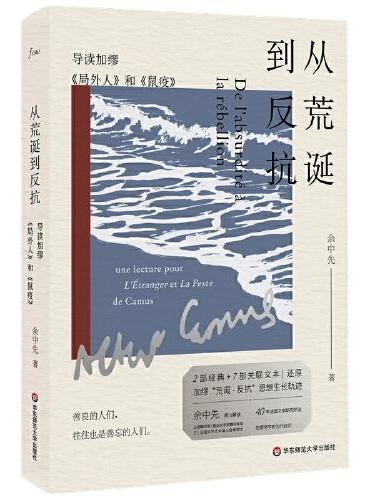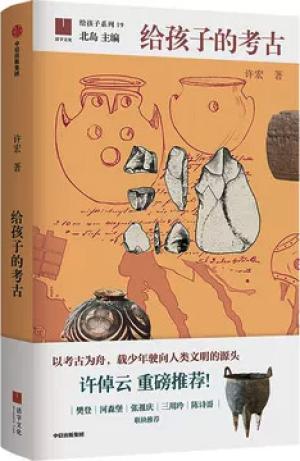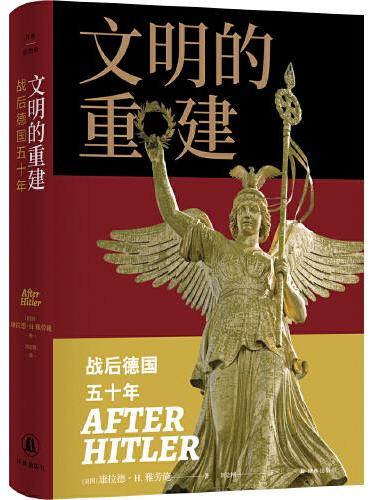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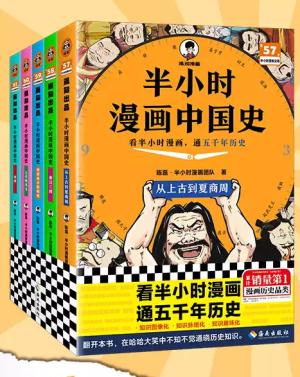
《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全5册)
》
售價:NT$
127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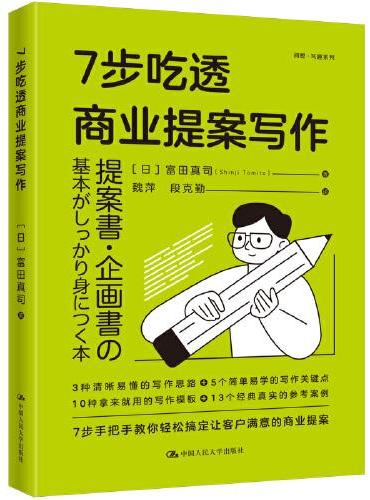
《
7步吃透商业提案写作
》
售價:NT$
3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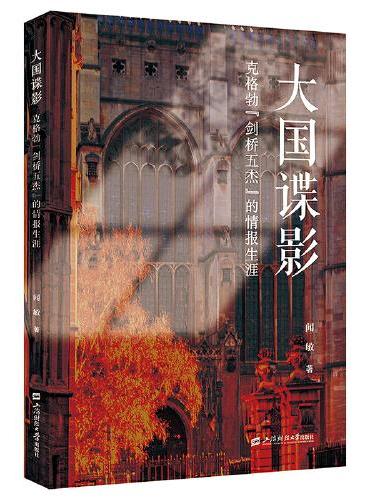
《
大国谍影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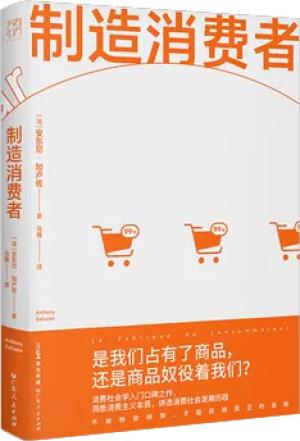
《
制造消费者
》
售價:NT$
2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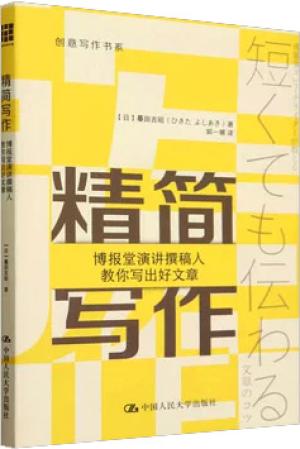
《
精简写作:博报堂演讲撰稿人教你写出好文章(创意写作书系)
》
售價:NT$
3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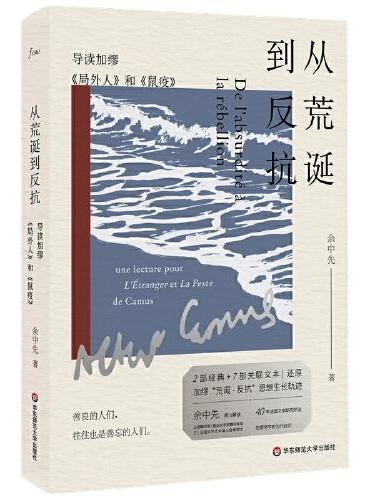
《
从荒诞到反抗:导读加缪《局外人》和《鼠疫》(谜文库)
》
售價:NT$
3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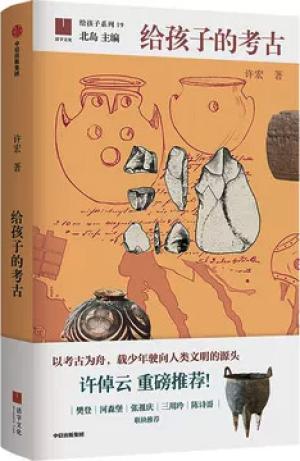
《
给孩子的考古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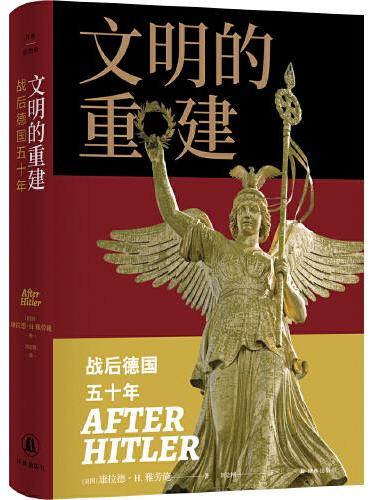
《
文明的重建:战后德国五十年(译林思想史)从大屠杀刽子手到爱好和平的民主主义者,揭秘战后德国五十年奇迹般的复兴之路!
》
售價:NT$
505.0
|
| 編輯推薦: |
1.一部全面剖析柳诒徵与南高史学群体的学术著作。王汎森、李帆、周佳荣、李金强联袂推荐。
2.深度挖掘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为南高史学研究开拓全新视野。本书既聚焦柳诒徵的史学观点、治史方法,解析其“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的史学要义;亦分析其弟子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郑鹤声等人的学术传承与创新,以“新史学”演进为背景,在与北大史学相比较的视野下解读南高学派,展现出南高的史学特色。
3.全面解析南高史学刊物,书刊、档案多重互证,诠释南高史学丰富内涵。本书详细解析《学衡》《史地学报》《史学与地学》等南高师生共创刊物,同时结合《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东亚各国史》等柳氏及其弟子之著作,辅以档案、校史资料等,全方位呈现南高史学研究者的观点。
4.以校史为钥,梳理南高史学发展脉络。全书以柳诒徵执教南高文史地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史学系的历程为主线,结合南高各时期课程设置、院系划分和教学特点,清晰呈现南高史学风尚孕育、成长、以致史地分途的过程,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南高史学发展脉络。
5.南高史学的坚守与融通,为当代学术研究提供启示。柳诒徵及其弟子以传统经学为根,既守护“礼”之文化命脉,又倡言“
|
| 內容簡介: |
|
一部全面剖析柳诒徵与南高史学群体的学术著作。本书聚焦柳诒徵的史学观点、治史方法及史学思想,同时分析以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郑鹤声为代表的学生群体对其学术的传承与创新。书中以南高发展历程为线索,系统爬梳学刊、校史等文献资料,整理出南高史学思想及发展脉络。他们以传统经学为根,既守护“礼”之文化命脉,又倡言“融化世界新知”,开创了一条中西融通的史学道路,与北大“疑古”史学和“窄而深”的治史思路截然不同。本书以“新史学”演进为背景,在与北大史学相比较的视野下解读南高学派,还原了民国史学的完整生态,为理解中国史学现代化过程中的坚守与创新提供了关键视角。
|
| 關於作者: |
|
区志坚,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田家炳孝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社会文化史、香港地区历史教研工作。
|
| 目錄:
|
导言 1
第一章 柳诒徵与南高治史风尚的形成 25
第一节 柳诒徵的生平及其学术27
第二节 清末民初师范教育的发展 54
第三节 江浙学风和江南藏书业的发展 63
第四节 反传统思想及中西文化调和论的出现 75
第五节 南高留美教员与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 89
第二章 南高史学系的成立与发展(1915—1925) 107
第一节 南高史学部的成立 108
第二节 南高史学部的课程 113
第三节 南高史学系学生概况 124
第四节 史地研究会及《史地学报》 128
第五节 学衡社与《学衡》杂志 135
第三章 南高史学者的分合关系(1926—1931) 141
第一节 《史学与地学》的出版 142
第二节 中大史学系成立及《史学杂志》的创办 148
第三节 《史学杂志》的内容 164
第四节 南高史学系出版物的流通及其特色166
第四章 柳诒徵的史学观点及其治史方法 177第一节 以礼为中心的史观 178
第二节 通史及“通则”“独造”的文化史观 193
第三节 信古的史观及反疑古史学 203
第四节 地方史及史地学的提倡 212
第五节 致用的考证方法 219
第五章 南高史学的继承与发扬
——缪凤林、郑鹤声、陈训慈、张其昀等人的史学研究 233
第一节 缪凤林的中国通史及中国礼俗史研究 237
第二节 郑鹤声的中国史学史及历史教育研究 257
第三节 陈训慈的地方学术史及中西史学研究 270
第四节 张其昀的人文地理学和地理教育学 282
第五节 其他从事史地学研究的南高学生 293
结论 310
附录一 1915—1923 年南高国文史地部教员表 321
附录二 南高史学工作者在《史地学报》发表论文数目表 323
附录三 南高史学工作者在《史学与地学》发表论文数目表 326
附录四 南高史学工作者在《史学杂志》发表论文数目表 327
附录五 国立中央大学的源流与变迁简表 328附录六 南高史学工作者大事年表 330
附录七 南高文史地部教员及学生照片(1923年) 332
参考书目 337
|
| 內容試閱:
|
李帆先生序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近代史学的多元图景
自从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特别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学院化、专业化、独立化为标志的近代史学基本建立起来。由于中国史学具有悠久、深厚的传统,此时面对和引入的西方思潮也纷繁复杂,故而在两者基础上建立的近代史学亦非以单一面目出现,而是呈现出多元性的图景。自然,多元性不意味着无秩序,内中有所谓“主流”和“旁支”之分。源自五四时期的北大、以胡适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学术纲领的“整理国故”运动,以及奠基其上的新历史考证学,如顾颉刚的疑古史学和傅斯年主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术研究,便居于史坛主导地位;而对之持有不同看法,代表所谓“保守”势力的“南高史学”,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师生所认同和坚守的史学,则成了所谓“旁支”。后来的学术史和史学史研究也往往依据时人的这种见解,更倾向于重视对“主流”的研究,而相对忽视对“旁支”的探讨,令人遗憾。可喜的是,区志坚教授所著《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一书的问世,将大大改善这一局面。
《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一书主要以柳诒徵执教南高史学部、东南大学史学系及国立中央大学史学系的历程为主线,以1919年至1923年于南高文史地部修读史学部课程为主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尤以张其昀、陈训慈、缪凤林及郑鹤声四人的治史观点及方法作为研究的重点。作者指出,柳诒徵及其学生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等人,在史地研究方面,尤其是在中国文化史、中国史学史、历史地理学及历史教育方面,各有其独特的成就,在中国史学研究日趋专业化的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值得我们对之进行深入探讨。柳诒徵的学问出自中国传统的经学,他凭借对中国典籍、历史,特别是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倡导历史撰述要肩负起重建传统文化、维护礼教伦理的责任,表明自己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深切爱护的态度。他一生著述繁多,被奉为南高史学的“精神领袖”。其弟子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等人,皆在学界独当一面,各有不凡建树。目前学界对于南高“学衡派”已进行过一些综合性的探讨,对于柳诒徵个人的思想、学术也不乏研讨,但对于由柳诒徵及其弟子所构成的南高史学群体却相对缺乏深入讨论,尤其是缺乏在“新史学”演进背景下,以及与北大史学相比较视野下的具体研讨,《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恰是在这方面多所用力之作,其弥补了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重要价值不言而喻。
在具体论述上,该书不乏独到见解。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史学的革命性变化,起自20世纪初的“新史学”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史学”分途发展,南高史学代表其中的一种方向。该书首先将这一点明确化,作为论述前提。在此基础上,该书充分论说南高史学的特色与价值。例如,基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定位,师范教育是南高的办学主体,文史地部师生受此影响,注重借史地研究推动道德教化,故多从宏观及致用的角度从事研究,努力推动贯通性的史地研究、史地教育的开展,实有异于北大“窄而深”的治史理念及方法,即更强调治学的博通而非专精;再如,基于对以北大为代表的“新文化”的反思,南高史学更注重以学术研究的眼光,来建构和解释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色,在“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之余,亦“昌明世界最新之学术”,不仅成为“学衡派”之主张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而且表明对于中国史学传统的更多坚守;等等。此类见解抓住了南高史学的主要特色,阐明了南高史学的独特价值所在,非常值得学界同行关注和借鉴。
总体而言,作为学界shou部全面探讨柳诒徵与南高史学群体的学术专著,该书可谓站到了学术前沿,创新性强,而且内容充实,个案鲜明,说理充分,叙述得当。不过尽管如此,该书的个别论述还是有再发挥的空间的。例如,南高史学与北大史学的分途发展,强调博通而非专精,就关联到民国史坛对于“通史”和“专史”研究取向的褒贬与判断,似应结合当时的讨论多展开一些论述;再如,南高史学对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关系的注重,实则关联到对史学研究中的一个老问题也是大问题的思考,即如何处理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书中对这方面的论述也稍显不足。当然,以作者的扎实功力和雄厚实力,相信他一定会在未来的研究中予以补充完善。
是为序
李帆
2020年1月18日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自区志坚:《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
柳诒徵的生平及其学术
柳诒徵是开拓和发展南高史学的关键人物,他早年的学习环境及其获得史地知识的由来,对于南高史学特色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作为东南方学术界的代表,柳氏与执教于清华大学国学院的陈寅恪并列,时人誉为“南柳北陈”,这位南高“精神领袖”的生平和学术是有必要首先加以讨论的。
一、早年接受中国传统学术熏陶时期(1880—1900)
柳诒徵生长在一个重视礼学及孝道的塾师家庭。五六岁时,其母口授唐人五七律。稍长口授四子书、五经、《孝经》、《周官》及《尔雅》等古文诸书。母亲令其天天背诵,逐日念书,书不背完,不能吃饭。与母相依,及得到乡邻接济生活,培养了他孝敬母亲、仁爱乡里的品德,长大后自号“劬堂”,就是不忘幼孤家贫,母教成才、终身自励的意思。母亲教课时,经常指出“为学之道,在明德”,故诒徵受母教的启发,以为“做诗做文不可好发牢骚,专说苦话,以及攻讦他人,触犯忌讳等等。所以平生谨守范围,固不屑以诗文为干谒谀谄之具,亦不敢用为玩世骂人之武器”,吾家“习于家庭礼法,亦从先妣舅妗后,承事惟谨”,因受其母的教导,柳诒徵由是孕育了以提倡道德教化为己任的思想。
除了母亲为柳诒徵提供了学术知识的来源,柳氏也受赵申甫及其父亲一位学生兼舅父陈庆年(1863—1929)所影响。在陈氏的教导下,柳氏由治经学转向治史学及注意通史研究。
在1898年之前,柳氏主要受母亲及外祖父的教导,并读书于镇江培风书院,治学以经书、骈文为主。乃至1899年,他结交赵申甫及陈庆年,治学自此转向史学。柳诒徵在《我的自述》中强调他在廿岁前后,“最得此二先生之力”,陈庆年听说他很好学,时常找他去谈论,他因而“得到许多讲学问的门径”。赵申甫是陈庆年的朋友,镇江人,因柳氏家贫,便常借家中藏书给柳氏,并经常与柳氏谈及镇江掌故,以及清朝学者的事迹,柳氏日后注意整理乡邦文献,与赵氏的教导也有关系。陈庆年为镇江丹徒县(今镇江市丹徒区)人,早年毕业于江阴南菁书院,长于史学,主要研究法制史、兵制史及地理学。他继承了清代考据学的研究风气,主张经学在礼学,认为实践礼学是重建秩序的工具,又宗浙东学者,言性命必折中于史,但处于清末这个列强入侵的时势下,陈氏认为士子应多注意研究通贯历代的史学,明了历代变化的原则,从而掌握治世的方略。他说,“汉儒欲救治经之弊,非玩经文存大体,求通今致用,宜取史学,如其事有关鉴戒宜少下己意为之发明,广取历代通事,观无涯涘”,所以他曾撰《兵法史略学》,并辅佐江苏巡抚端方,任幕府僚佐。陈氏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再次强调只考证文字的治经学方法,不足以处变列强入侵的时势,求通今必要提倡研治通史,以求通达古今,教员也可利用中国文明发达的历史知识,以振奋民心,增强民族自尊心,“以史教天下,即以疏通知远教天下”,“教育指归,至令人爱国而极矣,然爱国之理必先由于知国,盖治历史者之多少,验爱国心之多少”,“观通百代,处变时方”。为此,他也非常重视乡土的历史地理教材,认为“以仁爱乡土思想,而仁爱一县以渐被于全国”,《兵法史略学》一书就是在“通今致用,史学所急”的思想下写出来的,此书更成为晚清学堂兵学一科的教科书。陈庆年曾劝柳氏:“今世欲以辞章出人头地,曳曳乎难矣。曷至力经史根柢之学乎?”而柳氏也承认“陈善余(庆年)最深于史学,劝我(柳诒徵)不要专攻词章,因此我也就不大很做诗和骈文。陈(庆年)的志愿是讲学不做官,我也就只愿讲学不做官”,由此可见柳氏受陈庆年的经世思想和言论影响之深。
二、兼习中外史地知识时期(1901—1906)
1901年至1906年,为柳氏学习中西方知识的主要阶段。1901年,诒徵二十一岁,因陈庆年命录其骈散文十余篇,转交给任江楚编译局总纂的缪荃孙,诒徵的文章受到缪氏称许,故被缪氏任命为此局编纂,至1907年止。江南图书馆藏书除了中国史著作,在“史部”中,以收藏研究日本历史的书籍为大宗,共七十九种;其次为美国史,共十九种。由是柳诒徵不独因钻研馆藏那珂通世撰《支那通史》(此书以中文著述),而终成《历代史略》;更在任职编译局期间,阅读编译局及江南图书馆中所藏有关中国历史、日本史、东南亚史的典籍,而有一系列有关中国史地、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成果。
缪荃孙间接推动了柳氏对教育事业的注意。1901年,清政府宣布推行教育改革,同年12月,令缪荃孙与徐乃昌赴日本考察学务,次年1月,柳诒徵随缪荃孙等人,游日本横滨、大阪、神户及西京各地,尤考察日本的学校建制、课程改革、教材编写。柳氏在日本逗留至3月返国,其间他得知日本推行的教育制度与国家强大甚有关系,故立志以启导民智为己任。后来他接纳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宜先办小学和高等师范”的建议,于1902年7月与友人陶逊、陈义在南京创办思益小学堂,自任国文、历史、伦理、书法科教习。所以,随缪荃孙前往日本考察,使柳氏对教育事业的志趣大大提高。
此外,缪氏刻书及撰述,亦推动了柳诒徵撰述方志及研究地方史的兴趣的发展。缪氏曾参加《顺天府志》《湖北通志》《常州府志》及《江阴县续志》的编撰工作。柳诒徵也承认保存地方文献的思想,得自缪荃孙的启导,从中得到许多整理地方文献的门径。
三、从事教研工作及主持国学图书馆时期(1906—1937)
柳诒徵在此阶段致力于教育工作及学术研究,这对南高史学的发展尤为重要。1906年至1907年,柳氏以江楚编译局分纂的职位,兼任思益小学堂、江南高等学堂及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堂教习,开始参与教育工作。至1908年,两江师范监督李瑞清聘请柳氏任该校历史学门教员。两江师范的前身是1902年成立的三江师范学堂,这亦是日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前身,而校址即今天南京的东南大学。柳诒徵自1908年起执教于两江师范学堂,由是与师范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1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镇江也于11月宣布独立,驻江宁第九镇统制徐绍桢(1861—1936)亦宣布起义,进攻南京城,终取得胜利,却使两江师范大受破坏,校园设施遭到破坏,师生也未能上课。自1911年至1914年,柳诒徵也因南京战乱及学校受到破坏而避居镇江;1915年他回到南京,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之聘,任国文、历史部教员。江谦早于柳氏执教两江师范时,已欣赏柳氏行谊,自1915年任南高校长后,网罗人才,邀请柳氏任教其中。江谦更确立了师范教育的办学宗旨,并以南高作为东南地区教育学术发展的中心。
1918年郭秉文(1880—1969)继任南高校长,于1919年秋把国文史地部改名为文史地部,并于1920年推行专科发展方向,史学系、地学系由是成立。而柳诒徵也于1920年后成为史学部专任教授,柳氏借此学术机构以传播史学知识,并培训学生从事史学专科的教研工作。自1919年五四运动后,南高聘请了一群曾留学美国的学者执教文史地部,这些学者——如哲学部主任刘伯明,外文部教员吴宓、梅光迪。柳氏与吴、梅、刘氏更认为南高是一群反对过于激烈地批判传统文化,致力弘扬传统学术文化的“同志”的聚居之地。他们也因反对以胡适、陈独秀等人为首的激烈批判传统文化的言论,被视为“保守”的、“反新文化运动”的学者。
柳氏极力倡导学术研究,担任南高史地学部学生举办的“史地研究会”指导员,1921年与学生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等人创办《史地学报》;又与吴宓、梅光迪及刘伯明组织学衡社,出版《学衡》杂志。柳氏又为这些学术刊物撰写序或弁言,尤其是在《史地学报》上撰写的序,标举出了“史地通轨”的研究方向,及借学术研究以阐明中国文化的治学精神,这些研究特色均成为南高学生从事史学研究的指导方向。1923年南高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确立“师范教育专业”,特重教学、研究与教育事业相结合的发展方向,东大由是积极推动学术研究的风气。柳诒徵执教史学系,并开设中国文化史、东亚各国史、中国通史等科目,他要求学生读原著,记心得,撰写笔记,对学生的笔记,均能逐字眉批。顾颉刚在1924年发表论文讨论传说中的禹帝,认为其本是古代的“虫”,怀疑古代圣君贤相均是后人伪造的,由是掀起“古史辨”的运动;而柳诒徵也从文字的本义批判顾氏的说法,开了批评古史辨运动的先河。
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等学生,于1919年至1921年入读南高(东大),他们四人因为积极参与史地研究会举办的学术活动,以及积极在《学衡》《史地学报》上发表论文,故与柳诒徵及刘伯明、竺可桢等南高史地部的教员接触较多,治学方法上也显然受到柳氏等人的影响。
1922年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吴佩孚属下将领齐燮元围攻上海,江浙大战一触即发,结果齐氏大败。东大校长郭秉文因得齐氏资助,成功筹办孟氏图书馆,这使校内一些学者认为郭氏与齐氏有政治上的关系;加上,段祺瑞控制的北洋政府欲直接管理东大,由是支持“反郭”的言论,迫使郭秉文辞职,改任北洋政府所派的胡敦复为校长。而郭秉文对东大力行改革,甚得民心,学生多支持郭秉文复职,终于演变成学生们涌入校长室殴伤刚到任的胡敦复的事件,而校内方面也分成“拥郭派”“反郭派”。史学系教员徐则陵支持郭,反郭派的成员有杨杏佛、柳诒徵等。柳氏发表《学潮征故》及《罪言》二文,以为学生只有在安定的学习环境中才可上课,故应安处课堂,不应参与校园殴斗事件,此二文也表露出柳氏不满校董会负责人沈恩孚(1864—1944)操纵省教育会,以及批评郭秉文与士绅沈恩孚相为交往,使学术发展受到政治影响。最后柳氏更与萧纯锦、熊正理及段调元等教授发出《给教育bu总长函》,明确反对学生殴伤部聘校长。
结果政府派蒋维乔任东大校长,才结束学潮。而学生们认为,“教育bu突然更动我们校长,是因为校内有汉奸。汉奸是谁?就是柳翼谋”。柳氏因被学生指为与政治交结,愤而离职。
自学潮后,东大师生遇此“奇变”,纷纷离校。西洋史教授徐则陵,物理学家叶企荪,数学专家熊庆来,化学教授任鸿隽,心理学家陆志韦,生物学家秉志及地理学家竺可桢等人也离校。柳氏也因不满东大的校政及被学生指斥而离校。此后柳氏任教于天津南开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然而自1926年起,柳氏虽居北京,却因学生张其昀任教东大史学系,得以以东大史学系为文稿收集及整理的阵地,而郑鹤声及陈训慈也以东大史学系学生的身份,于1926年年初至1928年参与及协助《史学与地学》的出版,柳氏也欲以此刊物延伸《史地学报》倡议的“史地通轨”研究方向。
自1928年,柳氏因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馆长,遂返回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前身即东大,以下简称中大),并以兼任教授的身份执教于史学系,课余时协助缪凤林、陈训慈等昔日南高史学部的学生——当时已是史学系的教员,成立中国史学会。1928至1929年间,有感于执教中大地学系的系主任竺可桢创办《地理杂志》,并在此刊物的《发刊辞》上提出把昔日史学系开设的人文地理学及经济地理学两科,改由地学系开设,这样终将导致地理学独立发展,也会导致“史地分途”,实有违柳氏主张的治史方法,柳氏遂与学生以中大史学系的名义,合作出版《史学杂志》,并撰写序言,再次标举“史地合一”的研究方法,以相抗衡。
无奈,柳氏只得以兼任史学系教员的身份执教中大,他的工作地点仍是国学图书馆,不是史学部,故未能发挥南高时期领导学生的作用。也因为自1931年后,昔日一起合作及积极参与南高学术活动的学生,如张其昀已执教中大地学系,郑鹤声任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bu及国立编译馆,陈训慈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只有缪凤林以全职身份执教中大史学系,故《史学杂志》出版至1931年4月第2卷第5、6期合刊后,便没有再出版。
另外,柳氏自1928年任中大国学图书馆馆长。他为了世人可以得知馆中藏籍,并利用馆中藏籍进行研究,遂于1928年编刊《国学图书馆年刊》,柳氏在该年刊的发刊词中曾说:“诒徵无似,未尝攻图书馆学,承乏盋山,忽已经岁,既刊《馆章》(《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章》),缉馆史,理董馆书,增益而刊布之,爰综一岁中,同人黾勉图维讨议施行之迹,都为《年报》,贡之邦人,非以稽绩,昭不敏也。”编刊《国学图书馆年刊》的目的,就是把馆中藏书的数量及内容公布于世,以便国人借阅。又因为中大国学图书馆藏书来自江南图书馆及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为使世人了解国学图书馆的沿革及前贤的功绩,柳氏又撰《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其学生王焕镳、向达、范希曾等先后任馆员,又与柳氏一起为《国学图书馆年刊》撰写论文,而治近代思想史的学者蔡尚思,也因得阅馆中藏书而撰成《中国思想史》。
及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柳氏发挥了史学致用的作用,重刊馆中所藏由明代人物撰写的抗倭寇等典籍,如《经略复国要编》《辽事纪闻经略》《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以振奋民族抗战的精神。
四、逃避战乱及晚年生活时期(1938—1956)
1938年,柳氏逃避战祸,初到杭州,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请,与张其昀共事。及后,日军相迫,他只好再次经浙江、江西,绕道广东、云南、贵州,到达四川重庆,然而他未尝执教于四川的中大。在四川休养期间,教育bu组织清点文物委员会,令其负责考察地方文物及考订文献。柳氏更进一步整理多年讲授史学方法、中国文化史等课的讲义,准备撰写《国史要义》一书。1945年,他更被教育bu聘为教授。同年9月抗日战争结束后,柳氏复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1929年定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及党史会编纂。柳氏也曾致教育bu《接收收复区图书文物函》,指出“敌伪(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政权)对于公私书籍尽私人剽窃分据,而后汇为公藏”,建议“须对于敌伪劫去之图书文物,彻底追查,各归其主”,“严密关防,勿令彼方所留职员得乘我交替之时,隐藏盗窃”,对于“敌伪劫掠图籍不限地域”,展开全国调查,并与海外学者“订一共同办法,互相联络”,确保国人能接收流失的文物及图籍。1948年3月,柳诒徵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后,柳氏任上海市文物管理(也有称保管)委员会委员,整理委员会内的图籍,研究方向有所转变,专注于辑录奴隶史的资料,先后撰成《奴隶史料》及《人民生活史》。同时,他也进行辑录乡邦文献及校点《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工作,但因眼疾,致“目光日昏,不克多抄,又无写官相助,只可就力所能就者为之耳”。1951年后,柳氏与顾颉刚和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合力开办上海图书馆,又被任命为镇江市文物名胜保管委员会委员,直至1956年2月3日逝世。
综观柳氏一生,早年家贫,劳力自学,先从其母学习传统礼教思想及古代经籍,以传承中国传统礼仪、孝道为依归。及后,从陈庆年处“得到许多讲学问的门径”,因陈氏教导经世致用之学,又最深于史学,劝他不要专攻辞章,因此他“也就不大很做诗和骈文”。在陈庆年的影响下,柳氏自治经学、辞章转向治史学,喜通观历代社会、经济及民生的变化,以见当代治乱的缘由。同时,又因陈庆年的引荐,枊氏被江楚编译局总纂缪荃孙聘为馆中编纂,得以在局中接触新学;又从缪荃孙治方志学、目录学,“得到许多整理地方文献的门径”。柳氏因随缪氏访学日本,深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关系,乃于1902年开始办学,更于1908年执教两江师范,由是与师范教育结下不解之缘。终其一生,对史学研究工作从不倦怠,毕生的精力均付诸研究学术和推动教育的工作。作为南高史学部的“精神领袖”,柳诒徵可说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
——摘自区志坚:《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