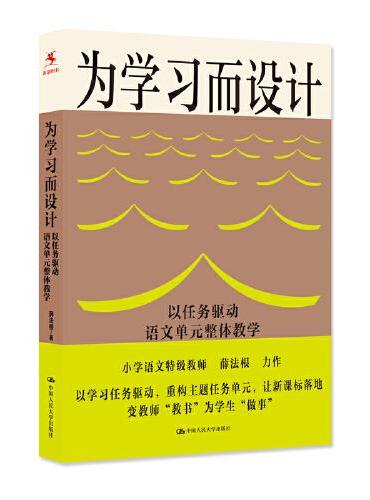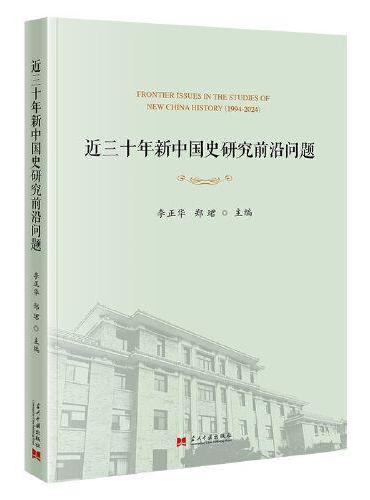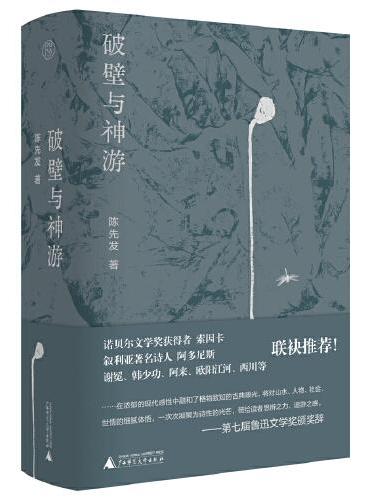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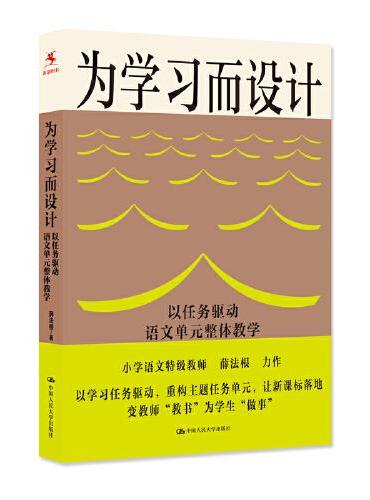
《
为学习而设计:以任务驱动语文单元整体教学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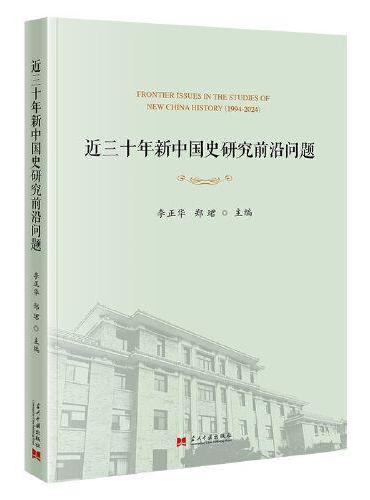
《
近三十年新中国史研究前沿问题
》
售價:NT$
500.0

《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
售價:NT$
4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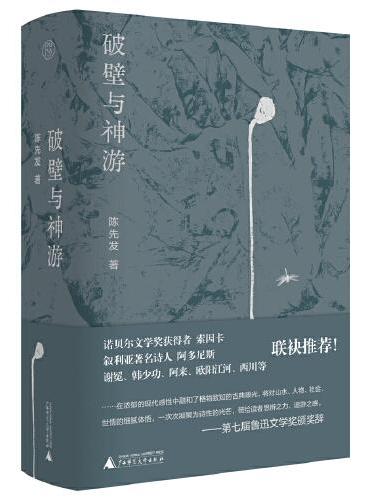
《
纯粹·破壁与神游
》
售價:NT$
418.0

《
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新版)
》
售價:NT$
449.0

《
女人们的谈话(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最佳改编剧本奖 原著!)
》
售價:NT$
286.0

《
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共域世界史)
》
售價:NT$
653.0

《
一周一堂经济学课: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
》
售價:NT$
500.0
|
| 編輯推薦: |
人气作家 钱塘路 酸涩治愈口碑代表作。
网络原名《今朝欢愉》
温柔哥哥江枫vs坚韧弟弟江晚。实体书新增出版番外《夏令营》。
随书赠送精美海报×1;小卡×1;双人拍立得×1。
我十七岁的这天,被烙上了一个永生的印,鲜活又炽热。
|
| 內容簡介: |
【经典语录】
我十七岁的这天,被烙上了一个永生的印,鲜活又炽热。
我迈出步子走向他,只不过这一次不再匆忙,因为他一直站在那里等我。在昨天,在今天,晚风里,日落前。
我仿佛长了两个心脏,左右同时跳动。他的为我,我的为他。
我像一只孤船,在江沨这条河里随波逐流,不知源头,不知尽头。
|
| 關於作者: |
钱塘路
双鱼座,有两只猫。
永远相信文字的力量,梦想是尽情写下去。
|
| 目錄:
|
第一章 初见
第二章 哥哥
第三章 回家
第四章 等等我
第五章 十七岁
第六章 不辞而别
第七章 好久不见
第八章 昨日永恒
番外一 日记本
番外二 好运气
番外三 除夕夜
番外四 夏令营
|
| 內容試閱:
|
七年后,我和江沨重逢了。
就在我牵着一年级(2)班的学生从学校里走出来的时候,他站在一年级家长等候区的最前方,西装革履,眉骨立体,头发全梳在后面,正在低头看表。
我不知道为什么能在人群中第一眼就看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只看到他低下头的侧脸,就能确信那是江沨,但我确实可以,从小到大都可以。
他和周围等待着的爷爷奶奶格外不同,不像是来接孩子的,倒像是准备参加什么大型会议。
即使我现在在教语文,也很难第一时间准确地描述我的感受。脚步一顿,我甚至想扭头就跑,然而还是晚了。
他抬起头,准确无误地直接看向我的眼睛。他的那双眼睛还是那么黑,颜色墨似的浓。
我手里拉着的领队的小姑娘突然蹦起来清脆地喊“江爸爸”,然后拉着我的手就往前冲。
这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我作为新上任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实在是不够称职,此时只能隐约地记起手上拉着的小姑娘叫江玥。
原来江沨已经有孩子了,我想。七年了,他也差不多该是这个年龄结婚生子了。
“江爸爸,你怎么来接我啦?”小姑娘把我拉到江沨面前后手仍没松开,另一只小手拉住江沨,脆生生地向他介绍我,“这是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江老师——”
还没说完,她又惊呼:“哇——你们都姓江啊!”
自从江沨抬起头跟我对视后,我就一直低着头不再看他,但是仍能感受到他落在我身上的目光。
这天是我上任的第一天,教务主任此刻一定正在学校的铁门后抱着胳膊观察,看我这个新来的老师究竟称不称职。
于是我弯下腰,尽最大努力平复呼吸,缓慢而温柔地对江玥说:“这是你爸爸吗?快回家吧,老师要去送一送其他的小朋友哦。”
我说完左手微微发力,从她的小手中挣脱出来。此时我才发现我的手心里都是汗,潮湿又黏腻,我忍不住将指尖在掌心用力擦过。
和江玥道过别,我把剩下的学生依次交给家长,挂上在镜子前练了三天的标准微笑和他们寒暄,顺便表扬这些我还没有记全名字的小不点儿。到最后,我的脸已经笑得有些僵硬了。
明明是背对着江沨,我却知道他仍站在原地——他在等我。
我应该直接离开,像七年前一样,但是脚下像是生了根似的,瞬间盘根错节,动弹不得。
况且教师公寓正好在他那个方向。
余光中,一辆商务奔驰停在学校门口,一位助理模样的女人把江玥带上了车。关门前,江玥大声地冲我喊:“江老师——再见!”
“再见。”我转过身和她挥手。
车开走后,江沨朝我走来。
说不紧张那一定是在撒谎,但我仍挂着没来得及收回的微笑,体面地开口:“好久不见。”
江沨闻言眉头微蹙,一言不发地拉过我,把我塞进停在路边的另一辆黑色轿车里。
九月初的春城暑意未消,仍是闷热又潮湿的,车内的温度却很低,我还能闻到淡淡的烟味。
江沨沉默地开着车,似乎没有和我交流的意愿。几秒后,我收回目光,把车窗放下两寸宽的缝隙,望着窗外呼啸而过的香樟树,深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才尽量语气平稳地开口:“好巧,在这里遇到你,你怎么会来春城?”
他仍没说话,连眼神也不给我一个,只是把另一侧的窗户也降下一些,专心开车。
半个小时后,车驶进城中的别墅区,绕过绿化带,停在一幢别墅外,江沨率先推门下车。
我正低头解安全带时门被拉开,他扣住我的胳膊把我拖下车,又反手摔上了车门。
“你干什么?”我扬声问,却得不到回答。
我跌跌撞撞地被他拽进别墅内,上到二楼,停在走廊尽头的房间门口。
手腕被攥得生疼,我忍不住挣扎起来,吼道:“江沨!你干什么?!”
听到这话,江沨终于转头看了我一眼,单手拧开门锁,声音低沉地开口:“老实待着。”
来不及反应,我已经被他推进门内,下一秒,房门关闭,又被上了锁,发出“咔嗒”的声响。
我忙握住把手来回拧动,又拍门继续叫江沨的名字,拍到手掌都发麻时才停了下来。我知道他不会回应我,继续下去也是徒劳。
没过多久,汽车的引擎声响起,我走到窗边向下望去,看见载我来的那辆车启动,缓缓驶出大门,声音由近及远,最后房间归于宁静。
又等了片刻,确定江沨真的离开之后,我环顾房间,试图找到房门钥匙,或是其他什么工具。
这间屋子很大,但也空旷,家具并不多,全部翻找一遍无果后,我坐在床边,后知后觉地感到疲惫。无论是第一天出任班主任,还是刚出校门就遇见江沨,桩桩件件的事情堆叠在一起,我的精力早已被耗尽。我放弃了试图逃脱这里的想法,倚在床头,想稍做休息,却在不知不觉间睡着了。
潜意识里,我知道这里不是我住的教师公寓,不该睡得太沉,但一闭上眼睛,我的身体就像是投进水中不断下沉,什么也听不到,看不到,感受不到了。
似乎是睡了长长的一觉,我醒来时,窗外已经完全暗下去了,室内也只亮着一盏廊灯。在不甚明亮的灯光下,我看见床尾一侧坐着一个人。
我坐直了些,再次看过去,真的是江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又坐在那里看了多久。或许是还没有从梦境中完全脱离的缘故,我几乎忘记自己是如何被他带到这里的,和他对视片刻后,我说:“你回来了。”
江沨没有说话,也没有动,有一瞬间,我甚至以为他是我的幻觉,于是又扬声叫他:“江沨。”
这一次,他终于有所回应了,起身朝我走来。
他还穿着下午见面时穿的那套西装,靠近后,我闻到了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烟味,不算浓烈,但我忍不住咳了一声,他听到后停在原地。
他很高,我需要仰着头才能与他对视,但光线实在是太暗,又被他遮挡住大半,我捕捉不到他的表情,模糊地与他对视片刻后,只听见他低声说:“你该叫我哥哥。”
听见江沨的这句话,有什么冰凉的液体顺着脸不断下滑,又滴落到手背上,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是我在流泪。
我并不想在江沨面前哭,忙抬起手去抹,泪却越流越多,眼前逐渐模糊起来,像是又回到了不久前的梦境中。昏暗的楼梯转角处,也有人对我说“你该叫我哥哥”。
我梦到了八岁那年的情景。
过完八岁生日的第二天,我被江怀生从边界的一座小城带走,前往海城。
飞机上,他帮我扣好安全带,又把毯子掖在我的腋下,低声说:“以后跟着爸爸生活好吗?你妈妈要去很远的地方,没办法照顾你了。”
早在妈妈把我送到他手上时,我就哭哑了嗓子,此刻一开口,我还打了个哭嗝,说:“妈妈要死了,我知道。”
他动作一顿,然后随意地摸了一把我的头发,被我偏头躲开。
我第一次坐飞机,不敢看窗外,但是更不想听江怀生以“爸爸”的口吻跟我说话,只能把脸转向窗外。
飞机离地时,巨大的轰鸣声让我不知所措,我只能紧紧地攥住书包的背带。
地面越来越远,最后缩小成像地图那样一块块的形状,我把头靠在窗上,闭上眼睛,心里想着妈妈,也想外公和外婆。再睁开眼睛时,我看到飞机冲破厚厚的云层正在下降,听到江怀生说“海城到了”。
至此,我离开了妈妈和外公、外婆。
下了飞机,坐上车,我又被江怀生带进一幢别墅,听到他说“到家了”。
江怀生的家有三层楼,和我家一样,但走进去我才发现,他的家里是多么华丽,像童话书里插图上的城堡。
客厅屋顶很高很高,连吊灯都是用水晶做的,吊灯下面有一架巨大的黑色的钢琴——我之所以注意到它,是因为有一个男孩儿正背对我们在弹钢琴。
我不知道他在弹什么,只是感觉钢琴的声音很响,他每按一下琴键,我的心也跟着狠狠地跳。琴声连贯起来时,我听到了风声,像是坐在妈妈的摩托车后座上,她载着我,穿越无垠的树林,抵达湖边,风把她的笑声送到我的耳旁。
霎时间,我变成了一块浸满湖水的海绵,被他的琴声挤压,于是湖水源源不断地顺着眼睛向下倾泻。
最后一个音结束,我如梦初醒,马上抬手擦干眼泪。外婆在跳跳童装店给我买的浅蓝色羽绒服的袖口处洇湿了一大片,变成了深蓝色。
我听到江怀生叫他:“江沨,过来。”
那个背挺得直直的男孩儿离开了钢琴凳,朝我们走了过来。
我见过他。
一周前的星期天,我照旧带着二年级的课本守在妈妈的病床前。其实二年级的课程对我来说已经很难了,尤其是背诵古诗词。
我趴在病床边,一边读“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一边看课本里的插图。老师说这是柳树,只是我从来没有真的见过,我们这里最常见的只有白桦和云杉。
读了两遍,我开始背诵时,不知道怎么回事,病房里的旧彩电突然接收到遥远的来自海城的信号,播放起海城的慈善晚会。
我和妈妈一起看过去。屏幕里,江怀生面对着镜头,宣布给海城市下属的县捐资修建两所小学。他说完话后,台下的人全都鼓起掌来。
屏幕里相机的闪光灯闪得我闭了闭眼睛。
外婆放在窗台上的收音机已经很旧了,声音总是断断续续的,此刻又抑扬顿挫地唱道:“无情无义真禽兽,有何面目出人头!”
“江怀生”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所在的小城里,连坐火车都不方便,流言的传播速度却像火箭一般迅速。
自我记事以来,邻居们只要见到我,总喜欢故作怜爱地摸摸我的头,说:“多漂亮的孩子,可惜——”然后几个人讳莫如深地对视,露出一点儿笑容,又改口对我说,“没事,去玩吧。”
慈善晚会播放到一半,妈妈从被子里伸出细瘦苍白的手,指着电视机对我说:“他是你爸爸。”
这是我第一次听妈妈主动提起“爸爸”。顺着她的目光,我再次看向屏幕,目光扫过江怀生,停留在站在他身旁的男孩儿身上。
男孩儿穿着一身和江怀生同款的黑色西服,领结闪闪发亮。他看上去比我大一点儿,很好看,比广告里的小模特还要好看,只是脸上一直没有表情。
我看着他,听不清江怀生究竟说了什么。没过多久,江怀生弯腰,把话筒递给他。我不禁竖起耳朵,想听一听他的声音,可是他刚张开嘴巴,信号又没了,屏幕上跳满了雪花。我觉得有一点儿遗憾。
此时此刻,电视里的那个男孩儿走到我面前。他果真比我大,也比我高,我只到他的胸口,只好仰起头看他,他却看向我的袖口。我连忙把手背在身后,低下了头。
他这天没有穿西服,也没有戴和水晶一样亮的领结,但仍然很好看,我又忍不住稍稍抬起头悄悄地看他。
江怀生拉过他的手,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心里,说:“这是江晚,你弟弟。”又对我说:“小晚,这是江沨哥哥。”
江怀生终于放开我了,我的手被他攥得发烫,幸好江沨的掌心是干燥的,带着一点儿凉意。
江沨握住我的手,把我往前牵了一下,然后问江怀生:“爸,我什么时候多了个弟弟?”
“一直都有,”江怀生对他说,语速有些快,“带弟弟上楼去玩吧。”
江沨看了看我,没有继续问问题,牵着我的手带我走上了楼梯。
屋子里很热,其实下飞机之后都很热,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冬天,这里却像春天一样暖和。
我想脱下羽绒服,但是江沨一直牵着我,我抽不出手。等上到楼梯的转角处,看不到江怀生之后,我才开口喊他:“江沨——”
他站在高一级的台阶上,转过头来。
他太高了,我连仰着头都看不到他的脸,只听到他说:“你该叫我哥哥。”
这一幕在往后的很多年里都常常光顾我的梦,没有明亮的光线,也没有精致的背景,像是匆匆拓下的一张旧胶片,承载了尘封十七年的过往。
那一年我八岁,江沨十一岁。
江沨继续拉着我上楼,把我带进三楼他的房间里,然后转过头,问我叫他什么事。
话音刚落,他似乎看清楚了我的脸,眉头皱起,用另一只手来蹭我的眼角,问:“怎么又哭了?”
他这么问,一定是刚刚看到了我擦在羽绒服上的眼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又哭了,其实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他的语气并不算十分友好,但是动作亲切,我几乎马上就信任他了。
我抬起胳膊,想自己擦掉眼泪,他却先一步拉住我的手,从睡衣口袋里掏出一块粉色的手帕递了过来。
看我没有接,他把手帕塞进我手里,说:“用这个。”
我看了看他,举起手帕,还没擦到眼睛,却先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带着一丝清凉的气息,像是夏天涂的痱子粉味道。我太热了,忍不住把手帕停在鼻子前,又嗅了嗅。
江沨有些不自在地问我:“你闻什么?”又解释道,“这是我妹妹送我的,女孩儿才用这个。”
外婆也有一块水红色的手帕,我点点头,认同他的话,把眼角的泪擦了。
我应该说一句“谢谢哥哥”,张了张嘴巴,却发不出声音来,像是喉咙里卡了一根生硬的鱼刺。
因为我隐隐地知道他是谁,是邻居们常说的“江怀生早有老婆孩子”的那个孩子,是江怀生“真正的”孩子。
江沨没有在意我的沉默,又问我几岁。我回答昨天刚刚满八岁。
“好小。”他坐在地毯上,拍拍旁边的空位置,招呼我,“快来,趁着江浔还没回来,我们把这个《哈利·波特》的城堡拼好,当作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