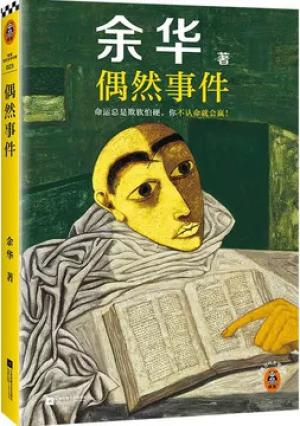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反卷社会:打破优绩主义神话(一本直面焦虑与困境的生活哲学书!)
》
售價:NT$
38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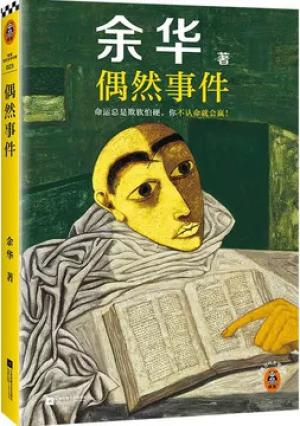
《
偶然事件(命运总是欺软怕硬,你不认命就会赢!)
》
售價:NT$
255.0

《
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2025)
》
售價:NT$
959.0

《
如何将知识转化为行动
》
售價:NT$
356.0

《
助人技术本土化的刻意练习
》
售價:NT$
408.0

《
中国城市科创金融指数·2024
》
售價:NT$
500.0

《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摆渡船上的人生哲学
》
售價:NT$
306.0

《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NT$
689.0
|
| 編輯推薦: |
|
父女关系对每一位女性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今我们却很少谈及,甚至是忽略了父女关系对一位女性的影响。软弱的父亲、专横的父亲、施虐的父亲、消失的父亲……乃至是父权社会本身就像是一位差劲的父亲,不论是个例还是源于文化层面,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都是当今社会的大多数女性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
| 內容簡介: |
作为一名心理分析师,琳达·希尔斯·莱纳德的办公室每周都会有心灵受伤的女性前来求助。她们中有些极端自卑,有些无法与他人建立持久的关系,有些对自身的工作能力和社会价值缺乏信心。表面看来,她们是自信满满的商务精英、衣食无忧的家庭主妇、无忧无虑的在校学生、潇洒不羁的离异人士……但在成功或光鲜的外表下,伦纳德看到的是受伤的自我、隐藏的绝望、无尽的孤独、对被遗弃和被拒绝的恐惧,以及从未停息的泪水和愤怒。
这些女性受伤的根源大多在于父女关系中的裂痕。她们有些是与自己的父亲关系不睦;有些是受到了父权社会的伤害,父权社会所倡导的文化贬低了女性的价值,本身就像极了差劲的父亲。无论哪种情况,她们往往通过选择被动服从(“永恒少女”)或防御性地模仿男性(“全副武装的亚马孙女战士”)两种模式来守住自己的生存空间,而她们的自我评价、身份认同,她们与异性的关系,以及她们在职业、智力和社交方面的表达能力也都将因此受到影响。
在本书中,莱纳德通过自己、来访者,以及梦境、童话、神话、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例子,揭示了父女关系创伤在如今普遍存在这一现象——这种创伤源于男性原则和女性原则之间混乱、失衡的关系。大多数情况下,世人普遍认为女人不如男人;男人若表现出女性特质,则极易遭人菲薄。男人和女人都深受其苦,双方对彼此的身份和角色都充满了困惑。
希望借由本书,能够呼吁女性开始关注父女关系对自己的意义。当一个女性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如何应对父亲的不作为和父爱缺位,并认清自身所处的关系模式时,她就能够摆脱这种模式对其生活的限制,进而寻求更真实、更有益的生活方式,促就自身的成长。这对于每个女性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
| 關於作者: |
琳达·希尔斯·莱纳德(Linda Schierse Leonard)
荣格派心理学家、荣格分析师区域协会(IRSJA)创始成员、畅销书作家
作为一名荣格分析师,莱纳德曾在苏黎世荣格学院接受相关培训,并拥有超40年的相关从业经验,积累了大量个案。
她参与创始的荣格分析师区域协会于1973年成立,至今已发展为北美规模最大的荣格分析师培训机构之一,拥有200多名分析师会员和大量学员。
同时,她也长期专注荣格心理学、女性心理的相关创作,著有多部畅销作品,其中本书与《烈火见证:创造力与成瘾的面纱》《遇见疯女人:赋予女性精神力量》已被翻译成12种语言,于世界各地出版。
|
| 目錄:
|
第一部分 创伤 / 1
第一章 父女关系中的创伤 / 5
第二章 献祭女儿 / 37
第三章 “永恒少女” / 55
第四章 “全副武装的亚马逊女战士” / 91
第五章 内在男人 / 131
第二部分 伤害 / 179
第六章 愤怒 / 185
第七章 眼泪 / 207
第三部分 疗愈 / 221
第八章 女性的多面魅力 / 225
第九章 救赎之路 / 235
第十章 发现女性精神 / 260
致 谢 / 275
|
| 內容試閱:
|
序
小时候,我非常喜欢父亲。那时的他温柔敦厚,对我疼爱有加,我最喜欢与他为伴。他带我打棒球,教我学数学。我七岁那年,每周六,他都会带我去图书馆。他还说服了管理员为我破例,让我每周借走14本书,那可是常规借阅限额的两倍。父亲自己没能读完高中, 但他极为看重学业, 所以他身体力行地让我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他和外婆一起花了大量时间陪我学习,他们帮我提高词汇量,和我玩智力游戏,变着花样教我学习各种知识。冬天,父亲带我去滑雪橇,跟着他,我看到了夜色下耀眼迷人的雪光,切实体验了快速滑到山脚的那种刺激和兴奋。他还带我去看赛马,在赛马场,我目睹了马儿飞奔疾驰的壮观场面,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押马赌博的惊险、激烈的气氛。父亲喜欢动物,受他影响,我也交到了很多动物朋友。父亲友好和善、喜与人交,我们一起外出散步时,总能结识到新朋友。因为有我这样一个女儿,父亲很自豪,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妈妈在他眼里也格外重要。每个周末,他都会带我们外出用餐,在我们居住的那座城市,我们吃遍了各种风味的民族餐馆。父亲经常带母亲去跳舞,他们会一直跳到深夜。那时,我们家在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我们的生活犹如华丽的冒险,有许多奇闻等着我们去挖掘,有数不清的趣事等着我们去体验。然而,不知何时,不知何故,一切都变了。父亲先是深夜不归, 回来就怒气冲冲、大吼大叫, 吓得我经常从睡梦中惊醒。起初,这种情况只是偶有发生,但很快就演变成了每周一次,接着每周两次,最后几乎夜夜如此。一开始,我很困惑,不理解母亲为什么总在星期天早上对父亲唠叨不休、百般挑剔,我甚至在心中为他打抱不平。九岁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父亲竟然是个酒鬼,左邻右舍尽人皆知!他连工作都难以维系。我真的为他感到羞愧。我有一张那时的照片,照片上的我和先前神采奕奕的我判若两人。那时的我看着像一个孤苦伶仃的弃儿,脸上没有笑容,眼里没有光彩,嘴角耷拉着,眉眼低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对父亲的感情一直都非常复杂。我还爱他, 但是, 因为他, 我备受煎熬, 甚至无地自容。我实在无法理解, 曾经那么美好的父亲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如此不堪。
父亲经常在深夜醉醺醺地回到家,扬言要伤害外婆。妈妈和我被逼无奈,通常只能叫来警察,强行把他赶出家门,而大部分时候,我就是负责打报警电话的那个人。有时,父亲情绪太过激动, 我没有机会靠近电话机, 惊恐万分中, 我只能逃到门廊上大声呼救。有一晚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晚,父亲异常暴躁,警察一来,就看到我蜷缩在角落里啜泣。一位警察转身质问父亲:“你怎么忍心让你的女儿承受这些?”显然,连陌生人都看不下去了,开始为我担忧。此后很多年,那个画面在我的脑海里一再浮现。甚至可能就在那一刻,在我心灵深处的一隅,这本书的种子已悄然埋下。
在我即将步入青春期时,我对父亲的感情已不再复杂,所有那些纠结的感受都凝结成了纯粹的仇恨。我不再爱他,甚至不再怜悯他。我厌恶他那些粗鄙的行为,恨之入骨。我向老师和朋友隐瞒了父亲的真实情况,所以我无法邀请任何人来家里做客。除了邻居,没人知道我的父亲是个酒鬼。我想,如果我守口如瓶,一定能盖好这块遮羞布。我和他彻底划清了界限,拼尽全力只为与他泾渭分明。
为了自保,我活成了“双面人”。在学校,我认真、刻苦,各科全优。作为老师的“宠儿”,我并未恃宠而骄,而是努力做到了友善、开朗、低调、包容,与同学们相处得极为融洽。表面上,我是可爱、文静的乖乖女;而我的内心却五味杂陈、混沌不安。我无法抑制对父亲的愤怒和仇恨,作为他的女儿,我无地自容,日夜担心有人发现我有一个如此荒唐的父亲。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一切看似风平浪静。14岁那年, 我开始出现面肌痉挛的症状,而且,我并未像其他女孩一样开始谈恋爱,我才意识到,或许我哪里出了问题。但由于我跳过一级,我在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矮,大家并未发现我的异常。在学校,我通过勤奋学习和讨喜的个性换得了一些慰藉,也找到了自我价值。但在家中, 生活就是一场场清醒的噩梦。每晚,我都在担心,那个疯疯癫癫的父亲会把我从沉睡中惊醒,但具体何时,我无法预料。我好害怕,某个夜晚,他会带着枪回来,把我们一个个都打死。
长大后,我决心逃离。我深知,留在家里就是坐以待毙。父亲像寄生虫一样蛮横地赖着我们,母亲为填补丈夫的情感缺位在我身上一味越界索取。为远离家中这令人窒息的喧嚣和混乱,我拼命地在知识和逻辑思维的世界搭建避风港。这一策略也使得我与母亲保持了足够远的距离。我意识到,如果我听从母亲的要求,陪她留在那种环境里,我将困在过去的牢笼中,永无出头之日。我试图切断与母亲和父亲的纽带,从那个我无力左右的家庭中脱身。
此后很多年,我始终保持着一种六亲不认的理性。事实证明,这招颇为有效。起初,我远走他乡,在科罗拉多州的一家小型日报社做了一名新闻记者。后来,我又研读哲学,锻造思维方式,以求更深入地探究生命的意义。大约在那个时候,我嫁给了一位学识渊博的男人。在我接触过的所有人中,他与我父亲最为不同。他鼓励我继续深造,努力攻读博士学位,勇敢踏上自己的学术之旅。
那几年,父亲的酒瘾越来越重。但出乎意料的是,我21岁生日那天,他竟然送了我一枚蛋白石戒指。蛋白石是我的生辰石。像他这样的无业游民本就没有经济来源,搞到手的每一分钱又都用来买酒了, 但不知怎的, 他竟攒下了25美元, 给我买了那枚戒指。那是多年来他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戒指很漂亮,蛋白石泛着神奇的光泽。但我不愿意戴。在父亲生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 我曾回家探望过他几次, 他多次问起那枚戒指, 我都只能闪烁其词。尽管心中歉疚不安, 但我依旧不愿戴。直到许多年后我开始动笔写这本书时,他已不在人世,我才鼓起勇气戴上那枚戒指。如今,我更是一直戴着它,希望能借此弥合我与父亲之间那深不见底的裂痕。
婚后, 我潜意识中被压抑的部分莫名爆发了, 焦虑和抑郁同时向我袭来, 如洪水猛兽般势不可挡。为了解读自身的遭遇, 我一一拜读了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和克尔恺郭尔(Soren Kierkegaard),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黑塞(Hermann Hesse)、卡夫卡(Franz Kafka)和卡赞扎基斯(Nikos Kazantzakis)以及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和荷尔德林(Friedrich H?lderlin)的作品。最终, 我翻开了荣格(Carl Gustav Jung)的心理学著作。出于职业性的自我防御,我打着立志成为心理治疗师的幌子去了苏黎世(Zürich),开始了荣格心理分析之旅。在这个过程中,潜伏在我体内的狄俄尼索斯(Dionysus)式的特质突然间涌现了出来。有一天半夜,我突然从噩梦中惊醒,那是我接触荣格心理分析后做的第一个梦,非常可怕。梦里有一艘搁浅的船,希腊人佐巴(Zorba the Greek)被吊在船椽上。但是, 他还没有被勒死!他冲着我大喊,求我救他下来。我慌了,手忙脚乱地折腾了一通,最终还是他自己费尽周折解开了绳子。但是,下来后,他还是伸出手拥抱了我。
这个梦让我心慌意乱,但不得不承认,对我来说,佐巴也象征着对生活的热情——一种逍遥自在、快意人生的狄俄尼索斯式处世态度。佐巴的生活让我想到了父亲,看到了一个人在失去理智、陷入泥潭后所遭受的致命暴击。由于我刻意疏离了父亲,压抑了自己非理性的一面,所以佐巴的世界在我眼里一度显得混乱、可怕和粗鄙。荣格将人类进入无意识状态的过程形容为“夜海航行”、死亡和肢解之旅,认为那是一种面对令人生畏的未知之域时战战兢兢的体验。确实,这正是我所经历的。踏入父亲的世界犹如纵身跃入深渊,虽不是什么可歌可泣的事,但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我也是被迫为之。我强烈感觉到,我在悬崖边站着时,有一个人悄无声息地站到我身后,一掌把我推了下去。跌入深渊后,我看到了自己的失常、醉态和愤懑。原来,我竟和父亲如此相似!很多时候,我的所作所为和他简直如出一辙。渐渐地,我开始任由自己在各种派对上喝得酩酊大醉,整个人也变得狂放不羁、肆无忌惮。在失控的世界里,我感觉自己被生生撕碎,像神话中的狄俄尼索斯一样。我的阴暗面彻底爆发了。在暗无天日的深渊中, 我苦苦挣扎。甚至在外形上, 我都和以前判若两人。以往,我一直留着精干的职业短发,而在那段时间,我特意留长了头发,逐渐向嬉皮士风靠拢。我在公寓内挂上了德国表现派画家的作品,那些画作色彩丰富、夸张怪诞,有些甚至让人不寒而栗。外出旅行时,我会故意在陌生城市的治安乱点挑选便宜的旅馆住宿。之前,我曾极力避开父亲的世界,现在我却一头扎了进去。终于,我也体验到了父亲曾经独尝的罪恶感和羞耻感。这一切看似如痴如狂,但我却莫名预感,那条路有宝可寻。在那段混乱的时期,我做过这样一个梦:
我梦见父亲住在一个地下室里。穿过一扇狭窄、破旧的小门,我走进了他的房间。一进门,我就看到斑驳的壁纸大片大片地从墙上耷拉下来,不禁浑身一颤。满是裂缝的地板上,油光发亮的黑蟑螂窜来窜去,仓皇爬上了一张棕色桌子的桌腿。那张桌子破烂不堪,是空荡荡的房间里唯一的家具。那个地方充其量只能算个小隔间,真不知道怎么能住人, 而且这个人还是我父亲。一想到这儿, 我的内心瞬间被恐惧淹没,我想逃离那个房间。我拼命地寻找出口,但借着昏暗的光线,我怎么都找不到那扇门,它似乎彻底消失了。我紧张得喘不过气,两眼疯狂地扫视着房内的每个角落。终于,我发现了一条狭窄的通道,就在之前进门处的正对面。那个房间阴森可怕、令人作呕,我急于逃离,没有多想就一头钻入了那条幽暗的通道。走到尽头时,光线突然照进来,我的眼睛被刺得一阵模糊。视力恢复后,我发现自己已来到一个庭院。我从未见过如此奢华的庭院,抬眼望去,花卉、喷泉和精美的大理石雕像熠熠生辉。庭院方正对称,位于一座东方宫殿式寺庙的中心,四角筑有藏式角楼。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父亲竟然还悄悄拥有这些。这简直匪夷所思,我陷入了惊恐和困惑,颤抖着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或许,父亲那肮脏不堪、蟑螂横行的地下室里确实藏着一个出口,径直通往那座金碧辉煌的藏传寺庙。要是我能找到那个出口就好了。
虽然我深陷泥沼,疯疯癫癫,无法自拔,但我还是挣扎着勉强维持了日常生活。然而,一个更为重要的发现闯入了我的意识。在那些灾难性的时刻,我的身体内竟然自然而然地流淌着一些神秘而美妙的体验。美术、音乐、诗歌和童话的大门逐渐向我敞开,我变得越来越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那之前,我腼腆、内向,只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闷头读书;自那以后,我变得松弛了,能够自在地展露内心的热情和感受。渐渐地,我变得更加自信,不再刻意隐藏真实的自我。
那段时间,家里连遭重创。醉酒的父亲在抽烟时睡着,引发了火灾,整栋房子只剩下一具黑糊糊的空壳。外婆被困在楼上的一间卧室里,不幸丧生。父亲曾尝试救出外婆,但为时已晚, 他自己也因严重烧伤被送进了医院。他一定内疚不已,余生都在炼狱中煎熬。因为无法面对这项过失,他始终未曾开口谈及此事。也许是因为常年酗酒,他的状态越来越差,两年后,他也去世了。
父亲的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悲从中来,痛入心脾。我忽然意识到,再也没有机会和他谈心了,永远没有机会告诉他我有多么后悔疏远他,没有机会向他坦承我后来其实也有些心疼他一生千疮百孔、备尝艰辛。我们之间没来得及修补的隔阂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一道伤口,一直无法弥合。
他离开后,我很快迎来了38岁生日。生日当天,我戴上了那枚蛋白石戒指,开始动笔写这本书。我并不在乎这本书能否出版。我知道,我必须将我们父女关系中的创伤付诸文字,这是我个人迫切要做的事。也许写作的过程可以适当拉近我和父亲之间的距离。客观上,我和父亲已再无亲近的可能;但主观上,我或许可以通过文字救赎我的“内在父亲”。写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动笔之前,我并非胸有成竹,甚至连提纲都没拟定。我就只是等着,相信一切终会水到渠成。我认为,写作需要全情投入,需要坚信灵魂深处自然会浮现出一些东西,而我有能力识别它们并立刻用文字表达出来。另外,我深知,无论我写什么,都有可能在照亮父女关系创伤暗角的同时,投下新的暗影。受认知所限,我肯定无法做到面面俱到,所以,我只能接受这种局限性和可能性共存的矛盾局面。巧的是,父亲的一生也挣扎在矛盾的旋涡中。在写作的过程中,我经常怒气填胸,也经常痛哭流涕。虽然成文的语句看似波澜不惊,但实际上每一页的字里行间都藏着我的怒火和泪水。
刚开始动笔时,我的脑海里浮现的大多是消极的画面。父亲生前酗酒成性、自暴自弃, 我意识到自己有蹈其覆辙的倾向。我能感觉到,这种“遗传”特质正左右着我的生活,它来势汹汹,浸渍肌肤,渗浃骨髓。我承认,父亲身上也有积极的一面,他也曾对我产生过正面的影响,但在写这本书的初期,这些影响在我的内心完全无迹可寻。写到“救赎之路”那一章时,我迟迟未能动笔。由理论的角度切入后,我得以从新的视角审视了我内心的冲突。在描述女性的各种生存模式和其原型基础时,我更好地理解了,这些模式如何影响和塑造我的生活以及我的那些女性来访者的生活。开始写自己的故事时,我对父亲那些正面的印象才完整地浮现出来。我记起了小时候他想方设法托举我、引领我,死后又以佐巴、藏传寺庙的形象在我的梦中给我力量, 而那枚蛋白石戒指在现实中也一直陪伴着我。神话中的伊卡洛斯(Icarus)一时忘乎所以,飞得太靠近太阳,高温熔化了封合他翅膀的蜡,失控的他一头栽落下去,命丧大海。从这个角度看,父亲很像伊卡洛斯。他也曾有望振翅高飞、鹏程万里,但他把远大前程淹没在了酒精里。他曾卖力地托举过我,这是他给予我的积极影响,但在他自甘堕落、判若两人后, 我看到笼罩在他身上的光环瞬间黯然失色。起初,我试图通过掌控一切来抹去他曾对我的托举;后来,当我发现我无法掌控一切后, 我认同了父亲自甘堕落的一面。我似乎只能在两个极端中取舍:要么360度无死角克己慎行,要么如狄俄尼索斯般任性恣情。认识到自己的极端心理后, 我分析了这两种心理模式, 我将这两种模式分别称为“永恒少女”(the puella aeterna)和“全副武装的亚马孙女战士”(thearmored Amazon)1。其实, 对我而言, 蜕变和救赎之路就藏在佐巴、藏传寺庙和那枚蛋白石戒指的意象中。我若想重获父亲的托举,就得在心里认可并安放好这些意象。
这些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女儿在父女关系中所经历的创伤。同时,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在工作中发现,许多女性来访者都曾在父女关系中受到过伤害。当然, 她们的遭遇不尽相同,创伤表象也是形态各异。许多女性来访者也提到了父亲酗酒,自己因此对男人不信任,觉得丢脸、内疚和自卑。从她们的描述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从另外一些女性来访者的经历中,我发现,严厉、专制的父亲或许能让他们的女儿过上稳定、精致、有序的生活, 但几乎无法给予女儿关爱和情绪支持,也不会重视和认可女性特质。还有一些父亲原本希望妻子生个男孩,所以就把女儿(通常是长女)当作儿子养育,期望她们完成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有些父亲太爱自己的女儿了,甚至拿女儿来填补爱人的缺位,这些女儿通常被父亲的爱所桎梏,无法心无旁骛地去爱其他男人,因而无法成长为成熟的女人。还有一些父亲选择了自杀,他们的女儿需要努力对抗自残和自毁的念头,以防步其后尘。父亲早逝的女性需要应对失去亲人的创伤, 活在缺失感中。父亲多病的女性往往会感到自责。有些父亲甚至会虐待女儿,比如殴打或性侵。还有一些父亲对强势的妻子言听计从,任由妻子主宰女儿的生活。
创伤不胜枚举。至此,有人可能会将这些创伤直接归咎于父亲。我们要提防这种粗暴的归因,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些父亲本身可能也在亲子关系中受到过伤害。创伤可能来自母子关系, 也可能来自父子关系。责备他人犹如身陷流沙, 绝非疗愈女性的良方。常怀责备之心可能会使人作茧自缚,沉溺于受害者的角色,无法自我负责。我认为,对在父女关系中受伤的女性来说,认清父亲的不作为和父爱缺位对自己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女性需要打破隔阂,修复与父亲的关系,以便有机会在内心形成一个正面的父亲形象。如此,她们才有望获得父亲这个角色给予的力量和指引,才能由衷地欣赏外在男性与内在男性的积极面。她们需要抱着开蚌寻珠的态度,努力挖掘出父亲身上不易察觉的优点,那是父亲可以给予她们的宝藏。如果父女关系已经受损,女性一定要看清这种创伤,觉察和识别自己的缺失,这样才能在内心生发出力量,有针对性地补苴罅漏。同时,看清这些创伤后,我们需要去接纳这些创伤的存在。因为接纳创伤就意味着疗愈的开始,对女儿、对父亲、对父女关系来说,皆是如此。
|
|